御春阁外,赏花亭里,一把长剑静静地躺在石桌上,虽有满地的鲜花却依旧掩盖不住它的冰冷与肃杀,一旁角落处,剑的主人正依栏闲坐斟壶自饮,花香芬芳,酒香醉人,而他却紧锁双眉,面色冰冷的就如他的剑一般,男子本喝不得酒,只因心有忧事得需酒消愁肠,此时难免就有了几分醉意,他抬头凝望阁楼,看着映在窗纸上耸动的曼妙身影,迷离如熏的眼神不觉变得火热起来,他心中愈发急切,已然有些不耐,此刻便是有再好的美酒都没了滋味。
终于,一声惊呼猛地从楼内传将出来,男子立时一震,神色激动起来,他飞身抓剑入手,迫不及待地纵身跃向阁楼而去。
“公子留步,这里你不能进去。”男子尚未进门,就被外面的侍女拦了下来。
“楼上怕要出事,我得上去看看。”男子心急如焚,说着横剑就欲将她扫开,不成想眼前这女子立身不退,反张臂来挡,男子本就不耐,喝声道:“滚开!”已是抓住她手臂运劲一提,将女子甩飞出去,紧跟着便闯门而入。
他大步向前,蹬蹬蹬几步就上了楼,一把推开房门,随即火急火燎的身形顿时震在了原地,只见房中偌大的一张床上,那名妇人正背身跪伏,雪白的身子一览无余,尤其是她那光洁溜溜的肥大屁股,迎面耸翘,其间桃源肉穴,湿湿漉漉纤毫毕现,直看得男子喉头滚动,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老爷,老爷,你醒醒,你快醒醒。”妇人正自焦心颤胆,伏在老人身边不住叫唤,此时听得身后动静,回头见是男子,不由双眼一亮,刚想求助,却欲言又止,反拉下脸来伸手扯了件外衣披到身上,这才冷声喝道:“放肆,郑兴,你好大的胆,竟敢擅闯御春楼。”男子慌忙低头,面露惶色,此妇人在他心中犹如神女一般,哪里敢有丝毫的违拗,不由小声道:“我、我只是担心你,怕你出事。”妇人面上闪过一丝柔和,却立时又转为冰冷,讥嘲道:“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来担心我?”男子听闻不免有些羞恼,终于仗着酒意全都发作出来,吼声道:“骆云霏,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明明知道我对你一片真心,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为什么?”他心中憋屈状如魔怔,径直走向妇人,好似有无数的疑问想让她回答。
“你敢吼我?”妇人心头一震,不意他今日变得这般大胆,眼见男子往自己处走来,不由惊得直站起来,脸上也有了些慌乱,“你、你别过来。”闻着扑鼻而入的酒气,妇人终于明白过来,脱口娇斥道:“你喝酒啦?”男子身形一顿,仿佛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般,变得期期艾艾起来,嗫嚅几声,这才扬声道:“男人喝点酒怎么啦,用你来管?”见她面露愠色,这好不容易壮起的胆又一下蔫了回去,嘟囔道:“你答应了我,不就什么都管得了了么。”妇人听得分明,不觉心中一叹也是颇为无奈,她知道男子喝不得酒,自然也明白他这十几年来对自己的心意,要说没动过念,那便是自欺欺人,可自己这身份,如何能应得了,倒不是因为瞧不起他,但既然当年与老爷有约在先,总不能忘恩负义,至少也要等老爷过世才能再作他想。
妇人想到此处又是一阵哀叹,不觉间已是萎顿坐地,看着身前的老人,一时复杂难明,她刚作了查验,情知已是无力回天,想自打跟他以来,老人的确对自己极好,虽然好色,但这男女之事不就是天下间最正常不过的事么,这十几年来,她尽心服侍,从未有过怨言,如今陡见他身死,竟有些心灰意懒起来。
男子见她面容黯然,着恼之余又于心不忍,只得安慰道:“你也用不着难过,欠他的你早就还清啦,现在死了,正好可以放下。”妇人轻叹呢喃道:“终究是夫妻一场,这么多年怎能说放下就放下呢。”
黄蓉光身赤裸躺在一边,自打男子推开房门,起初还有些羞恼,但见他两眼只顾盯在妇人身上,这才心下稍安,等听了一阵两人谈话,竟不觉有些泰然起来,此时听得老人身死,不禁忘了自身的尴尬,愕然开口道:“什么?老头儿死啦?”
男子转头看去,不禁为之动容,但见这位绝色女子玉体横陈,酥胸挺拔,私处饱满,全身皆是妙处,不由得多看了几眼,直到对方恼怒瞪眼,这才点头道:“不错,老头儿死啦。”
黄蓉心下好奇,问道:“刚才还威风来着,怎么说死就死啦?”
男人回道:“就是太威风,才马上风死的。”
黄蓉又问:“马上风是什么?是病?”
男人不耐烦道:“就是脱阳,纵欲过度。”
黄蓉哦了一声,似懂非懂,妇人却是心中一动,对老人的身体状况她自问清楚得很,按理不该得此脱症才对,她心中起疑,看向男子道:“你来得倒巧,难道早就知道会出事?”
男子避开她目光,神色讪然道:“怎、怎么会,我刚才听你叫喊,这才上来看看。”
妇人见他心虚,愈发坚定自己的猜疑,正色道:“回春丹的药效你我都清楚,绝不会让老爷如此失控,郑兴,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你们万毒教做了手脚?”
男子着慌,连连摆手道:“不不不,不关万毒教的事。”妇人心中一凛,暗道果不其然,立时追问道:“那关谁的事?你?”
男子急道:“不、不关我事,要是我,怎么会忍到现在,早把他杀了。”
妇人自然也知不会是他,暗自点头道:“那你说,到底是谁要害老爷?”
男子脖子一梗,道:“你别问了,反正我不知道。”
他平时虽对妇人唯唯诺诺,但真要犟起来十头牛都拉不回,不然也不会苦等妇人十几年。
妇人也知他这脾气上来再难相问,正自气恼无奈,忽听旁边“噗嗤”一声,却是黄蓉发笑道:“你这汉子,连谎话都不会讲,任谁见了你这模样,都知道你晓得是谁啦。”
妇人被她这一打岔,终于面色一缓,柔声道:“郑大哥,我知道你恨老爷,但老爷对我有救命之恩,青儿能健健康康长大,也是全靠老爷当年费尽心力四处求药,这是咱娘俩欠他的,老爷不嫌我未婚有子纳我为妾,但仅凭我这副残柳薄躯,又如何能还得清这份天大的恩情,现在他又死得不明不白,你让我如何对自己交待,对刘府交待?”
她顿了顿,叹声又道:“我知道你的心意,人非草木,这十几年来你对我的爱意我一直记在心上,但我不能对不起老爷,所以一直对你不假辞色拒之千里,本是想让你知难而退不要平白耽误一生,既然事已至此,你若还不嫌弃我这残败之身,我也该允了你才是。”
男子心中一荡,跨步走到妇人跟前,激动道:“当真?你真的肯答应我啦?”妇人点头道:“我答应你,不过在将我娘俩托付于你之前,我总得给老爷一个交待,你若是真心对我好,就该了了我这桩心愿。”男子迟疑了片刻,看着面前这个端庄玉润又风韵流溢的美妇,终于心中一横,道:“是你那个金兰姊妹柳红棉,是她在回春丹里做了手脚。”妇人闻言只觉脑中嗡地一声,犹自不信,口中呐呐道:“不、不可能,她没理由要害老爷,为什么?”
男子嗤声道:“为什么?还不是为了你,她这么做就是想逼你加入欢喜教。”
妇人瞠目作色,责问道:“你既然早就知道,为什么不通知我?”
男子叹息一声,道:“她答应我,事成后就会撮合我们。”
妇人一怔,心底的怒气便再也发作不得,一时黯然伤心,过得片刻,这才又道:“单凭这还不足以牵制我,接下来她还想做什么?”
男子回道:“让我嫁祸吴掌柜,挑起你跟万毒教的仇恨。”
妇人已然明白,冷笑道:“到时再由她出面保我?”
男子点头道:“不错,那时不但万毒教要寻你,刘府也要找你,你又不能在江湖中露面,只能寄身于欢喜教。”
妇人心中暗想,但凭自己这性子,只怕到时果真会跟她加入欢喜教,一时只觉心灰意冷,叹道:“想不到我这位妹妹,将我算计得分毫不差。”
男子咧嘴笑道:“现在没事啦,去他妈的算计,咱们什么都别管,找个地方躲起来安生,岂不比神仙还美。”
妇人也觉当下只能如此,暂且不说能否打得过那位欢喜教的堂主,便是胜了,真要动手杀她,到底是多年的金兰姊妹,只怕到时自己也下不了手,只能心中作罢,看着眼前老爷的尸身,不觉神色茫然道:“世间这么多的虚情假意,只怕就你是真心待兰儿好了。”
她话语沧桑,仿佛心间有无数的伤心往事,男子心中吃味,哼了声,道:“你放心,我会比他对你更好。”
妇人也不理他,只顾拉过被单盖住老人全身,好似作了最后的道别,这才起身从床上下来,站到他跟前柔声道:“你别生气,我既然答应了你,以后自然也会尽心对你。”
男子心中一荡,看着眼前朝思暮想的美人儿对自己如此温柔,又见她松散的外衣底下,从前襟处涨裂欲出的大片雪白乳肉,一时间只觉豪气顿生,如何还能忍得住,伸手一把就将妇人揽进怀里,随即凑上脸去吻那两片娇艳的红唇。
“唔……唔……”妇人冷不丁被他吻住小嘴,感受着口中横冲直撞的大舌,只觉呼吸不畅,心跳如麻,好不容易推开他,这才娇喘道:“你、你这浑人,也不看看时候,怎么就敢胡来,还怕以后没机会么。”
男子却并不放弃,再次抱住妇人,一边埋首在她颈间,耳鬓厮磨,亲吻舔舐,一边已扯掉妇人仅披在身上的外衣,攀上她胸前,握着那团只手不能掌覆的大奶,揉搓抚捏,抓挤掐拽,怀中温润,手上丰弹,男子不觉粗喘闷声道:“霏儿,我想你想得好苦,每天做梦都在想你,我要,我现在就要,求求你,给我,也给我一次。”
两人功夫只在伯仲,妇人想要挣脱也非难事,但此时忽听他发自内心的真话,当下心便软了,感受着耳旁的火热气息,又察觉出厮磨在底下的那根如铁坚硬,妇人知他此刻性致正盛,已是情欲难遏,若是不应了他,只怕一时难以善了,不由得心中暗叹,既然打定主意要跟他,也早做了侍奉他的准备,此时给他又有何妨,索性反手勾住男子脖颈,轻嗯一声,也去吻他脸庞。
男子经她授意,越发激动起来,赶忙舍了手中那团软肉,急匆匆就去掏自己的阳根。
裤子未脱,肉屌已弹翘而出,男子随手塞好长袍前摆,挺臀便刺。
感受着腿间的坚硬好似无头苍蝇般的乱撞,妇人不由伸手捉住,微分双腿,引其入户。
“滋”的一声,随着男子屁股一挺,阳根已全根没进妇人的牝户里。
男子只觉自己屌儿进入了一片温暖逼仄的软肉堆里,润润滑滑包裹无间,酥麻的快感立时从肉棒传遍全身。
妇人亦是屄里一紧,顿觉火热充实,坚硬饱胀,感受着牝户内的跳动,当真是前所未有的活力,一时也是心中满足,舒服不已。
“嗯……”
“喔——”
两人异口同声,呻吟而出。
男子挨将不住,开始抽插。
两人一个光身赤裸,一个衣衫未除,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立身交合起来。
楼中侍女本就是妇人的心腹,虽知老爷身死,又见主子与别的男人苟且,倒也并无其它心思,黄蓉更是全不在意,反觉好奇有趣,笑盈盈躺在一旁只顾看戏。
就在妇人酥骨动听的呻吟下,男子渐渐奋力起来。
妇人被耸得站立不稳,只好抬起一条腿来勾住男人后腰。
如此又弄了一阵,男子这才顿住身,粗喘着休息。
“你、你把我放到床上去,也省力些。”妇人娇喘道。
男子嘿然笑道:“瞧把我笨得,都干糊涂啦。”说着抱着妇人将她顶到床边。
妇人娇媚风骚地嗔了他一眼,坐到床上,这才招呼呆立一旁的侍女道:“你们两个傻丫头,还不快过来替郑爷宽衣。”
男子乐得有人伺候,刚脱光身子,这才猛然想起一事,惊道:“楼下那翠丫头,我来时还守着不让我进,怎的现在没声响啦?”他虽知这些侍女是妇人的亲信,但保不准她们变心,那丫头没追上来,不会是跑去刘府叫救兵吧?
妇人也有些迟疑,对其中一人道:“小红,你下去看看。”那侍女应了声,下楼而去,只一会儿,又急怱怱跑上来,慌道:“夫人,不好啦,小翠晕在外面醒不过来啦。”妇人吃了一惊,拿眼询问,男子讪然挠了挠头,委屈道:“我只是将她甩到一旁,没伤着她呀。”妇人着恼的责怪一眼,赶忙起身披衣,正欲下楼而去,男子拉住她,可怜兮兮道:“不做啦?那我咋办?”妇人瞪他一眼,又见他胯间的昂首凶物,没好气道:“忘不了你吃的,我待会儿上来。”临走又吩咐另一名侍女道:“小绾你留下,替郑大爷吮啧会儿。”说着便自下楼去了。
那侍女转身跪到男子胯前,抬脸俏生生道:“郑大爷,让小绾来服侍您吧。”说着俯过头去,张开小嘴就将那阳根吃了进去。
男子身子一挺,喔了声,只觉暖暖湿湿,柔柔软软,当真是好生舒服。
黄蓉啐了一口,看着侍女伸缩着脖子吞吐,想不明白这男人的肉棍儿有什么好吃的,怎的这些女子都想着吃,脏兮兮的还吃得这么津津有味。
侍女口舌灵动,想来不曾少吃,男子被她啯得快感连连,不觉便在她嘴里挺动起来。
就在一片稀里哗啦声中,妇人已抱着小翠走上楼来,她将昏迷的侍女放到床上,找来药喂了,这才放心道:“磕到台阶了,幸好无碍。”
男子从小绾嘴里抽出阳根,走过去查看了一番,也道:“的确是幸运,不然平白无故就伤了条人命。”
妇人坐到床边,道:“算你还有点良心,要是死了,我心里又要愧疚。”
男子笑道:“不是没事儿么,甭担心啦。”他见妇人俏脸上抿起的一对娇艳艳的唇儿,挺胯到她面前,腆脸道:“霏儿,你也替我吮啧吮啧吧。”
妇人看着顶在自己脸前的肉屌,媚眼一抬嗔怪一眼,随即低头含将下去。
“滋啧、滋啧……”
男子身子打颤,快感不知比刚才强了多少倍,看着心心念念的美妇吞吐着自己的肉屌,只觉快意非常。
“当年青城四杰的云中仙子,竟在用嘴巴吃自己的屌儿,我这是在做梦么?啊——”男子心中长啸,此刻尽是说不出的畅快得意。
“唔——”妇人螓首一压,娇哼声已将阳具整根吞入。
“嘶——”男子倒吸了口凉气,全身立时绷紧起来,只觉肉屌挤进了一片更加窄小,更加柔软的膣道中,紧箍异常,舒服透顶。
如此僵直片刻,妇人这才“哗”地一声吐出喉间阳根,不及喘息,就又吞了回去。
男子嘶哈着气,颤声道:“霏儿,你这做夫人的,本事果然比她们大多啦。”
妇人听他调笑自己,口不能言,只能愈发的卖力,好似拿它出气一般。
也不知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还是男子实在太过激动,如此刺激下,泄意竟突如其来。
就在妇人吞阳入喉的当儿,男子精关陡然大开,阳精喷薄而出。
“唔、唔、唔……”妇人感受着喉间的滚烫激射,只得滚动喉头,将阳精吞咽入腹。
男子泄阳在妇人嘴里,心有不甘又怕她责骂,本欲抽身撤回,却见妇人抵口不退,一时邪念顿生,抱住她脑袋狠命一顶,射了个痛快淋漓。
妇人整张脸面被男子摁在胯间,嘴里又塞着肉屌,只觉再也呼吸不得,好在她毕竟身怀武功,内息一起,倒也勉强能忍。
男子射一波,妇人便吞咽一次,果然是做夫人的本事极大,竟未倒灌一滴。
等男子舒舒服服的射完,妇人这才吐出这根令她无法呼吸的祸根。
男子尚不过瘾,伸手抱来,又想要干。
妇人赶忙拦手道:“时间不多,咱们还是早做准备,你想再要,还怕没了机会?”
男子一顿,这才作罢。
两人穿好衣服,妇人来到黄蓉身边,解了她身上穴道,开口道:“不管你是否愿意回如意楼去,这御春阁你是不能呆啦,是去是留你自便吧。”
黄蓉四肢得动,舒了下身子,坐起来欣然道:“你真的放我走?”
妇人笑道:“我自顾不睱,又何必多管闲事。”
那郑兴男子也走过来,见黄蓉喜形于色,不由瞅了眼她两个袒露饱满的奶子,道:“丫头,你也别高兴的太早,吴掌柜能放你出来,想来已经给你吃了蚀骨散,你就是再不想回去,只怕到时也身不由已啦。”
黄蓉惊道:“什么蚀骨散?我中的不是十香软筋散么?”
郑兴嗤声道:“要单单是十香软筋散就好啦,省得你到时疼得满地打滚。”
妇人也是一惊,对男子道:“就一丫头,吴掌柜不至于给她下蚀骨散吧?”
郑兴道:“你别小看了她,这小妮子有几分功夫,下手狠着哩。”
妇人哦了一声,这才认真打量几眼黄蓉,摇头叹道:“若是真的中了那蚀骨散,确实难办了。”
黄蓉见他们说的骇人听闻,不觉也凝重起来,想起当初那大奶女子的害怕,料来说得就是此毒,她虽然着慌心切,面上却摆出一副不屑,晒笑道:“有什么好难办的,我找姓周的拿解药不就成啦。”
郑兴嗤道:“周瑾与吴掌柜自己中着毒都没解药,哪里拿得出来。”
黄蓉一呆,惊道:“姓周的也中着毒?她不是好着么?”
郑兴道:“这蚀骨散每三月发作一次,平时看不出来。”
黄蓉道:“那三月后呢?没解药又会怎样?”
郑兴凛然道:“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之后全身骨骼慢慢融化,死状极惨。”
黄蓉听得不寒而栗,接着问道:“想必姓周的不止三月吧,她怎么还活着?”
郑兴道:“万毒教自然会送药来给他们。”
黄蓉笑道:“这不就成啦,到时我抢过来便是。”
郑兴嘿了一声,也不知这丫头哪来的自信,讥嘲道:“你说抢就能抢来啊,要这么容易,万毒教早散啦,更何况那也不是真正的解药。”
黄蓉聪敏过人,稍一动念便明白其中关键,想来这蚀骨散是万毒教拿来制人的手段,不由点头道:“真正的解药在万毒教手里,难不成我得去找他们教主要?”
郑兴道:“那倒不必,吴掌柜的上头是李长老,他那里一定有。”
妇人摇头道:“想要从万毒教手中抢解药,谈何容易,你小小年纪便是武功不弱,但要对付李长老这种教内宿老,只怕也是千难万难。”
她本性善良,看着眼前与自己女儿年纪相当的黄蓉遭此劫难,早已动了恻隐之心,不由喟然叹道:“我本不该坏了瑾丫头的好事,但既然要离开这是非之地,也算是给老爷积点功德吧。”
说着站起来往旁边柜架上取出一罐瓷瓶,接着道:“这是十香软筋散的解药,至于将来能不能取得蚀骨散的解药,就全凭你自己的本事了。”
黄蓉心中一喜,笑盈盈道:“谢谢你啦。”这才接过药吃了,妇人也不闲着,伸掌往黄蓉胸间按去,一边揉抚一边解释道:“这解药需行经心脉方能奏效,你不能运功,我帮你引气疏导。”
郑兴看着妇人的手在黄蓉雪白娇嫩的双乳间游走,一时起了邪念,嘿嘿一笑,也伸手出去,腆脸道:“我也来帮你,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妇人见自己的男人调戏别的女子,只嗔怪了一眼,却并不阻止,反收回手来便于他轻薄,想来她长年久浸御春阁的淫戏,对此已是习以为常毫不介怀了。
黄蓉亦是不以为意,她连日来不是赤裸与人交欢,就是任人摆布抚摸,本就对男女之事犹如白纸一张懵懂无知,所经历的又是这等淫乱场面,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时只道这男女之事也不是什么紧要大防,于贞节更是不曾想过,看着男子抚摸着自己的胸脯,反而侧目轻笑道:“你这痴汉,先前给你摸你不要,现下倒要争着来摸啦?”
郑兴搓着手中的嫩乳,笑道:“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先前我还没得到她,怎么可以要你。”他倒也不是纯粹占便宜,手上运着真气的确是在帮她引气疏导,方才动念,也只因黄蓉的绝美姿色,真要说淫欲,在他心中,哪里比得上旁边大奶大屁股的妇人。
黄蓉经他这一番揉搓,顿时心中火热,只觉有一丝丝暖流从胸间扩散开来,慢慢流遍全身,接着汇聚到小腹丹田,随着男子的搓弄越聚越多,最终盈满饱涨,倒灌全身。
“嗯——”
黄蓉舒服地长吟一声,立觉气力充体浑身是劲,不由猛地出手去扣男子手腕,郑兴见机极快,立时低手一翻,屈掌为爪,只往上一送,就要去反抓黄蓉,他武功毕竟高出黄蓉许多,这上下一对招,霎时就抓住了黄蓉的手腕,黄蓉任他拿着也不管,用另一手发掌去打男子,郑兴早就等着她,曲臂一抬,又将她握住了。
黄蓉双手被制,只得瞪着他气鼓鼓娇喘,“小妮子,就这点本事,还想去抢万毒教的解药?”
郑兴心中得意,正自取笑,余光却见白影一闪,知她横腿扫来,此时他坐在床边,两手抓着黄蓉倒不如说是黄蓉抓着他,当真是避无可避,只好撒手跳开。
黄蓉坐直身笑道:“你看,总有法子不是。”妇人在一旁见两人打闹,不禁摇头道:“既然十香软筋散的毒已解,那也是该分别的时候了。”她转头又对男子道:“我在这边收拾一下,你去接青儿回来。”
郑兴应声,取了剑兴冲冲下楼而去。
再说周瑾一行人在酒楼里斗的正酣,两边谁也奈何不得谁,孟珏眼见对方棘手,只得暂且收剑跳出战圈,他把剑收入鞘中搁到旁边桌上,又从腰间取出一把短锥,一柄小锤握在手里,这是青城派的独门武器,最擅近身肉搏,此时拿来对付这钻山虎倒是极为合适。
青城派远居四川,少有在江南走动,张大魁又是地头蛇从未离京,是以并不知晓这两柄武器的厉害,见他拿出小锥小锤,不由晒笑道:“怎的,打不过爷爷要改行做铁匠啦?”孟珏听他讥讽,心中已是大怒,面色不觉阴沉下来,他也不说话,只把锥尖悄悄对准张大魁,随即钢锤猛地往锥底一敲,只听嗤的一声劲响,一枚钢针急射对方胸口而去。
张大魁虽言语轻视,但心神却并未放松,此时陡听破空之声,急忙翻身滚到一边,但两人相距甚近,暗器又来势迅捷,哪里避得来及,只怕“噗”的一声,已被钢针射中。
“他奶奶的,这是什么暗器?”张大魁坐起身,捂着肩头咬牙问道,想不到这暗器如此强劲,竟钉入肩骨让他再也抬不起手来。
孟珏冷笑道:“青城派,青蜂钉,等会儿下了地府,跟阎王爷可别报错了名字。”这是先前张大魁对他说的话,此刻,他原话奉还。
“青城派的青蜂钉,果然名不虚传。”正当孟珏想要再次击发钢针之时,一个娇媚的声音从外面传将进来,随即便有名女子跨门而入,姿容妖艳,身段妖娆,走路如杨柳摆风,举手投足间,竟有种说不出的风骚浪荡。
女人面上带笑,虽显轻挑,却又不觉让人亲切,“这是唱的哪一出呀,莫不是奴家进错了门,酒楼改成戏台子啦?”孟珏眉头一皱,摸不清对方来路,一时也不好再出手。
众人见女子到来,不觉都停了手,周瑾移步到司马如琬身边,悄声道:“这女人是欢喜教的柳红棉,行为不检,似乎与恶虎帮有些往来。”司马如琬见这女子搔首弄姿,早已心中不悦,此时又听是什么欢喜教,单听名字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不由暗骂一声,“狐狸精。”
两人说话本就小声,没想到女子耳力极佳听得分明,只见她掩嘴咯咯一笑,走到司马如琬近前,细声细气道:“奴家既然生而为女子,自然只求男人的宠爱,这天经地义的事,你怎么就说人家是狐狸精呢。”司马如琬只觉身前沁香扑鼻,耳中柔音绵绵,不觉呆了一呆,等回过神,这才心中一凛,赶忙缩手入袖。
柳红棉见她这小动作,扫了眼她袖子,笑问道:“袖里乾坤?司马家的家传绝技,想必姑娘就是司马岱老英雄的女儿啦?”司马如琬吃惊道:“你认识我爹爹?”柳红棉道:“有幸认识,不但认识,还相熟的很哩。”说着又掩嘴媚笑起来,司马如琬见她这般轻浮放浪,不由将信将疑。
孟珏听她相识掌门,不敢怠慢,赶忙过来见礼道:“原来却是前辈,不知前辈尊姓大名,等日后弟子回到门中,也好向师父他老人家请示。”柳红棉打量了他几眼,点头道:“都说青城的青蜂难测,松风难躲,司马英雄倒是教了个好徒弟啊。”孟珏听她夸赞,不由直了直腰,面上却谦恭道:“前辈谬赞了。”
柳红棉笑道:“你也别前辈、前辈的叫啦,这无端端地就把人家都叫老了哩,其实人家也大不了你几岁的,叫我柳姐姐也好,红棉姐也行。”孟珏见她这扭捏娇俏的模样,没来由心中一荡,竟生出一股邪火来,下体不由就是猛地一跳,他暗舒口气,赶紧弯腰称呼道:“孟珏见过红棉姐。”
这柳红棉乃是欢喜教红袖堂的堂主,极善交际奉迎,专门连络拉拢江湖豪杰权贵富贾,长袖善舞,最是会看人眼色,孟珏脸上的刹那失态,又怎会逃得过她的双眼,只见她看似不经意的扫了眼孟珏的胯间,随即媚眼一飞,咯咯娇笑道:“孟兄弟一表人才,这一声姐叫得人家心里欢喜得紧呢。”司马如琬见他们眉来眼去,心中恼怒,不由上前站到自己夫君身旁,板脸道:“你说你跟我爹爹相熟,我怎么却从未听他说起过你?咱们司马家可不认识为虎作伥的朋友。”柳红棉见她说得直白也不介意,只笑道:“贤侄若是不信,大可去问问你爹,想来司马老大哥也不至于忘了我这个妹妹。”她说着走到周瑾跟前,终于正色道:“你我之间虽然总得分个胜负,但短时间内怕是很难,也绝不会是在今天,回去告诉你家掌柜,胃口好能吃是好事,但前提也得要有个好身体,否则吃撑了肚皮,也是要死人的。”她作为欢喜教此地的管事,周瑾的底细如何会不知,此时倒也没有揭穿。
周瑾自知无论武功与地位都远不及对方,又见青城派的两位弟子与她甚有渊源,哪里还敢久呆,告辞一声便拉着青儿出门去了。
柳红棉这才叹了声,对夫妻俩道:“京城之地水深凶险,个中的关系错综复杂,这恶虎帮能在天子脚下相安无事,背后又怎会少了官府的势力,咱们江湖中人虽自命逍遥无羁,但真要惹了朝廷,又哪里还有自由。”孟珏深以为然,点头道:“晚辈受教了。”司马如琬虽心中不服,却也不得不深感无奈。
柳红棉又走到张大魁面前,背着俩夫妻又嗔又媚的瞪了他一眼,道:“你们恶虎帮虽不至伤天害理,但平时也没少横行霸道,这次就当是教训,还不走?”张大魁两眼在柳红棉身上打了个转,嘿嘿一笑,点头哈腰道:“我走,我这就走。”说着打了个招呼,一群人扶的扶,搀的搀,灰溜溜出门而去。
却说周瑾与青儿出了酒楼,不敢闲逛,径直往如意楼回去,此时夜色更深,两人越走越静,眼见离着如意楼不远,一辆马车从对街缓缓驶来,周瑾心中虽疑倒也并不在意,就在双方错身之际,几个黑影忽从马车上跳将下来,不由分说便往周瑾扑去,周瑾心里一惊,情知对方有备而来只怕自己难以应付,本想暂避先回如意楼再说,可有青儿在侧,一时退避不能,只得迎身而上,刀光剑影间几个交手,周瑾便已暗暗叫苦,这三人武功本就不弱,又互相配合,自己如何能敌,正勉力支撑,当中一人却绕过她抓向青儿,她不由心中一急,长剑格开左侧刀锋,就欲闪身相救,门路瞬时又被另一把刀所阻,她自顾不睱,只能眼睁睁看着青儿被那黑衣人拦腰扔进车里。
那人得手也不恋战,驾上马车便离街而去,周瑾想要追赶,却苦于身陷战圈无法脱身,很快马车便消失在街角深处,剩下两人又与她纠缠了一阵,这才纷纷跳开各自逃往不同方向,刚刚还打做一团的街上,顿时只留下周瑾一人独自站立当场,她垂手四顾,一时间只觉心乱如麻,茫然无措。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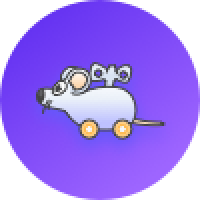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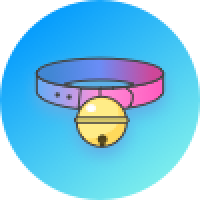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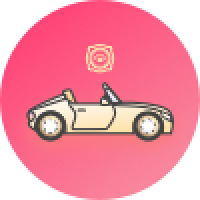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