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清晨,不顾杨余思的挽留,沈云笯匆匆穿了衣衫,偷偷摸摸回到客栈小院。
沈云笯刚走进厅堂,就看到阿鬼坐在桌前喝粥的身影,她脚步一顿,蹑手蹑脚走进去。
阿鬼抬头扫一眼沈云笯:“吃饭了吗?”
沈云笯捂着肚子干笑:“没有呢,还没有吃。”
阿鬼点点筷子:“坐下吃。”
沈云笯半边屁股粘在小凳上,端着碗看着阿鬼傻笑:“阿鬼,我昨晚没回来,忘记跟你说了,哈哈。”
阿鬼轻轻点头:“嗯。”
沈云笯松一口气,她给阿鬼夹个小包子:“嘿嘿,阿鬼,让你担心了。”
阿鬼扫一眼沈云笯:“你跟杨余思在一起,我不担心。”
沈云笯脸一下爆红了,她端着碗脸埋进粥碗里,脸热得直接冒热气了。
阿鬼端着碗喝口粥说道:“杨余思算是良配。”
沈云笯埋头吃饭,她又忍不住抬头,傻笑道:“是吗,阿鬼,我跟你说,昨晚我们去放了河灯,还吃了好多本地小吃。”
沈云笯双眼发亮,端着碗:“阿鬼,你去放河灯了吗,水面全是星星点点的花灯,映照在河面上,就像是天上的银河倒悬,太美了。”
沈云笯捧着碗傻笑:“阿鬼,原来杨余思轻功那么好啊,能直接踩在水面上呢,昨晚他给我取的花灯,岸上小姑娘都看着他。”
沈云笯说了几句,自己捧着碗吃饭,脸上笑意融融,乐呼呼的像个小傻瓜,阿鬼看着她叹口气,给沈云笯添菜,自己几口把粥喝完。
按照行程,今日从临清出发,沿着运河南下,阿鬼与沈云笯打包好行李,沈云笯站在岸边,看着滚滚江水。
阿鬼将马车卖了,提着大包行李往船舶上放,临清登船,直下江宁,只需月余可达,还少去路上颠簸,阿鬼预备着途中下来,带沈云笯再走段陆路,免得她沿途乏味。
沈云笯提着一盏花灯,已经没有了蜡烛,她站在栈桥边回望远处,江面大风吹乱了她的断发,阿鬼站在船沿看着她。
身后是繁华的临清北市,耳畔全是船夫的吆喝,波涛声中,沈云笯低头看着手中莲灯,她抬头对阿鬼笑笑,起身跨过栈桥,站在船舶上,沈云笯拂开船帘,俯身往里走起。
“云奴!云奴!沈云笯!”沈云笯睁大眼,她起身望向岸边。
杨余思骑着马奔来,骏马嘶鸣,沿途的柳枝被他带起的风拂开,岸边抱着刀剑的浪人,捂着嘴娇笑的佳人看着他。
杨余思从马上下来,他站在栈桥上,看着船舶上的沈云笯,“你怎么走了,我到处找不到你。”
他额头全是汗,一眼也不敢移开眼的看着沈云笯。
身后熙熙攘攘的临清市集全部潮水般褪去,沈云笯眨眨眼,她举起河灯:“我要走了,河灯要顺着河流,不能一直停留的。”
杨余思急的满头大汗,他隔着短暂的江水喊话“可是,可是我抓住了河灯,我将河灯送给了你,云奴!你收下了!”
杨余思在栈桥上弯腰握住沈云笯手腕,他在滔滔江水与喧闹人声中颤声喊道:“你能不能不要走!”
沈云笯闻言展颜一笑,她踮起脚揽着杨余思脖子,隔着江河船舶吻在他唇上,柔软的嘴唇分开,沈云笯摆手大声道:“余思,再见。”
阿鬼叹口气,摆手示意船夫开船,杨余思呆呆站着,沈云笯断发飞舞在风中,她站在船边挥手:“再见!”
直到再也看不到人,沈云笯还满脸笑容的看向远方,阿鬼低声道:“别笑了。”
沈云笯转过头来,笑意盈盈,眼泪毫无征兆掉下来,“抱歉。”
阿鬼叹口气,他抱住沈云笯,沈云笯伏在阿鬼肩上痛哭,撕心裂肺得像是要把自己所有痛苦挣扎全部哭出来。
阿鬼拍在沈云笯后背,“你后悔了我们就回去。”
沈云笯伏在阿鬼肩上痛哭摇头,怎么能回去,回到何处去,哪里可以安身立命,这世间只有三妻四妾,哪里有一女多嫁,回去沈林川怎么办,沈敛怎么办,杨行止怎么办,若是怀着孩子,杨余思怎么办。
夜里,在波涛声中,阿鬼唤来人寄出了一封信,临清有圣教大量散落的势力,阿鬼的出现,很快便集聚了人群在身边。
阿鬼熄灭烛灯,他听着隔间外沈云笯辗转的声音,决定再写一封信,旁人隔岸观火总是要清晰些,命运已经足够残酷狰狞,何苦还要自己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寥落的庭院间雨滴沿着屋檐低落,杨余思趴着石桌上,湿冷的空气笼在院中,他面前摆满了酒坛,满院的酒气。
杨余思眼角绯红一片,脸侧的轮廓干净清晰,长剑丢在桌上,剑客高扎的发髻如一匹黑绸垂落下来,遮挡住他半边脸庞,劲装窄袖利落得丝毫不像他落魄的样子。
杨行止踏进来,他搬开散乱的酒坛,坐在杨余思面前,杨余思趴在桌上,抬眼看着身旁的杨行止,他吐着酒气,声音飘飘摇摇:“大哥,我没有强求,我放手了,大哥。”
杨行止摸出木雕递给杨余思,杨余思吐着酒气接过,他看着手中笨拙小巧的木偶,双眼微眯:“这是什么?”
“是云奴,我雕的。”杨行止拿起一旁的酒坛,他找到还有酒的,仰头灌下。
杨余思手撑在下巴上,眯着眼打量,他看着看着红了眼,杨余思手捂在脸上哽声道:“嗯,蛮,蛮像的。”
杨行止仰头喝一口酒,摸出信放在桌上:“走吧,我们去找云奴。”
杨余思抬头看着杨行止,半响后拾起信就着屋檐的灯笼细看,他再抬眼,廊下的灯火摇晃在他眼里,灿如星河,杨余思站起来,他拿起剑四顾:“就这样走?”
杨行止点点头,抬步往外走去。
沈敛抱剑立在门边,他看到人出来,点点头,三人一起消失在夜色里。
第二日船舶靠了岸,沈云笯晕船吐的厉害,虽然她坚持要乘船,并表示习惯后就好,阿鬼还是拉着她上了岸。
沈云笯在小院中郁郁寡欢,她强颜欢笑,阿鬼出去后她还是挂不住笑容。
傍晚时靠的岸,阿鬼见沈云笯吐得脸色惨白,想要她夜里在客栈修整,便包了一处小院,但他自己却转眼不见了踪影。
沈云笯手捂在小腹上,她心里算着日子,想着与沈林川最后欢好的时候,越想越是慌张,万般事物堆在心头,千头万绪她竟不知道如何是好。
弯月升上枝头,星辉满天,沈云笯撑着手站起来,她叹口气,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夜色中传来悠悠笛声,飘飘渺渺散在风里,沈云笯立住脚步,她抬头看向远处,听得入了神,以往杨余思也是这样吹笛给她听,只是后来却再也没见过了。
沈云笯手抚在窗台,神色伤感,她听了会转身要走,却抬头看到坐在墙头吹笛的杨余思。
明月高悬,墙外繁枝伸出墙头,夜风幽幽,杨余思坐在墙头横笛吹奏,夜风吹拂起他的衣袂,他坐在高处,眼中含着千山万水,看着窗台后抬首的沈云笯,一曲笛声慢慢散在风里。
沈云笯抬首看着他,恍惚是在梦中,杨余思跃下墙头,立在窗台外,伸手向着沈云笯。
沈云笯睁大眼看着他,慢慢伸出手来,杨余思隔着窗台握住她手掌,俯身抱住沈云笯,低喃散在沈云笯耳边:“云奴。”
沈云笯恍惚点头,回抱住杨余思,“嗯。”
“我来找你,我把大哥和沈敛都带来了,云奴。”隔着窗棂,杨余思环抱住沈云笯,他抱起怀中娇人,手中用力,将人抱出窗棂。
沈云笯惊呼,她搂住杨余思,在衣袂裙摆翻飞间,如轻灵的小鸟投入杨余思怀里。
杨余思抱住沈云笯,他低头吻在沈云笯额头:“云奴,云奴,云奴。”
一声声的低喃溢出,沈云笯仰着脸喟叹,迷醉在杨余思温柔里。
杨余思抱住沈云笯,心口饱涨,温软的感情要溢出心口,他低头吻在沈云笯脸颊:“云奴,我想你,能不能不要走。”
沈云笯胡乱地点头,她抱住杨余思,心神像是飘忽在云间,软得一塌糊涂。
杨余思低头吻吻沈云笯,他扶着沈云笯,“云奴,我和大哥还有沈敛都来了。”
沈云笯转头,却被拥入另一个宽阔的怀抱,低沉醇厚的嗓音响在耳边:“云笯。”
沈云笯埋在杨行止怀里,她听着胸膛里沉稳的心跳,就像脚踩在了大地,慢慢变得平和踏实,沈云笯抬起头望向拥着自己的杨行止。
杨行止深邃的眉眼印刻着沈云笯的身影,他缓缓露出笑容,抱着沈云笯举高,“云笯。”
沈云笯环住杨行止脖子,惊叫道:“当心摔着。”
杨行止轻笑:“不怕,抱的住你。”
沈敛站在一旁,他抱着剑像个影子,看着沈云笯与人嬉闹,眼中慢慢露出笑意。
沈云笯回头:“沈敛呢?”
沈敛走出阴影,沈云笯含羞看着他:“你一直都在啊?”
沈敛点点头:“嗯。”
沈云笯羞愧地眨眼,伸手要沈敛抱。
沈敛抱住沈云笯,侧头吻在她脸庞。
沈云笯抱住沈敛,算了,放不下就放不下吧,人尽可夫就人尽可夫吧,不在乎了。
杨余思弯腰看着沈云笯,他俊朗的面容露出愁容,支支吾吾好半响:“云奴,你腹中的孩子,你不要吃药,你才生产不久,又大病,若是再小产,你的身体受不住。”
他手握在胸口,看着沈云笯又苦恼又诚挚:“云奴,你好好养胎,把孩子生下来,我们一定视如己出。”
沈云笯心口滚烫,她正要答话就感到下身一股热流,她抚在自己小腹上,脸色一僵,“不,不必了。”
“啊!”杨余思拉住沈云笯,“云奴,你听我说,你把孩子生下来,我们再去接回小乖乖,云奴……”
沈云笯捏捏杨余思脸颊:“我去更衣。”
说着吻在他脸庞,转身小跑进屋内。
三个大男人面面相觑,跟着也进了屋。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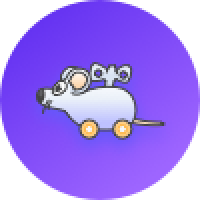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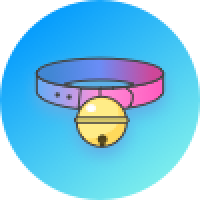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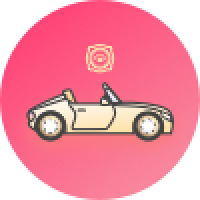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