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夕相约的一万年之期,没想到先背弃的会是我自己。
我还曾担心我的人生对夕来说过于短暂,她不久便会觉得无趣。
罗德岛事务繁杂的那些日子里,我根本顾不上同她定下的,随叫随到的约定。所幸迟到一两天还不会激起她的脾气。
一次我迟到许久,发现她已经入睡。等上一整天,她还未醒来。
她曾说没有我她难以睡眠,想来不过是信口开河。还是说我在她闺房待得太久,让她变得这么油嘴滑舌。
只得是感叹道,美梦仙,枕思眠。到我离开前,她都未曾睁眼看过我一眼。
我晓得,我于她根本是朝菌蟪蛄。
夕曾理解不了的短命的人们,她有想过我也是其中一员吗?“弗愿去想”,我还记得她娇蛮肆意的答案。她可知道她下次睁眼,人间又是何时春秋,哪个年月?我的人生,却再长不过两个五十年。我不能说我喜欢曾经那个担惊受怕,不敢入睡的她,她的那副样子可怜兮兮。但不论凡尘,完全超然的她,我却等不起。
渐渐我变得愈发迟钝,刻意疏忽了她的召唤。她也似乎明白蜉蝣的烦恼,唤我没有再那么频繁。
为什么她弗愿想凡人苦恼,她一定也曾遇见过一些自顾自离开她的人。我也该从她身边逃走,享受俗世百年吗。是吧,正因为我等不起。若是夕也明白我的意思,她就该返了天庭,算好一个甲子后再来看看我是否活着,是否成家,又是否已经安然辞世。
但我回到房间时,却见了她的障眼法了。
夕身着墨绿色,绣上黄金游龙纹的无袖旗袍,挂好红色年结耳饰,如漆的黑夜般的长发,分出几缕扎结成发环。她穿上了她不擅长的高跟。赤红色令人心醉的眼眸转向我。青墨染尘烟。
我还惊讶于夕为何会出现在我的房里。她见我看得痴呆,也就嗤嗤笑起来。
我问夕为啥突然上门。
“咋个,你的房间,还不准我进了?”她用我熟悉的炎国方言戏谑言道。
我说岂敢岂敢,只是她似乎是来过兴致,把我整个房间都涂鸦了一遍。现在我的房间里正树立着不少炎国墨宝中常见的歪脖子植株。
“喝酒。”她回道。
“为啥子不去找你的令姐。”
“为啥子不能来找你。况且那令姐喝不醉她,好生无趣。”
“只有喝酒?那我还有点心力。”
“没有心力,便陪我困觉。”
我不知道该如何给她喂话,直说在和她如胶似漆的热恋期过后,我想离开她过凡人生活吗。我正想开这个口时,她手指点住我的嘴唇。
“你没有必要现在说话。”然后她开心地笑起来,仿着我们一起看过的大炎戏曲的唱腔道:“相公,可否为小女子去取一枝寒梅——”
我房间里自然本不该有梅花的,但她画出来了,就画在墙壁上。我伸手,真个摸到了梅树那纤细枝条,一折、一回头,我却已经在她的画中了。她邀我入画的手法每每都这么别致。
“入座吧,三杯便好。”
我曾也讲过夕的习惯,流觞曲水,饮酒颂词。
每每一顿痛饮,又要一阵大脑运功。但引人发笑的应是,夕的酒量连我都不如,往往是第二杯过就倒在我怀中。今日她说三杯便好,可她本就过不了三杯。
她要我第一杯,狡猾的神仙妹妹。
一杯天禄。饮尽后杯盏放回流水中,流回水墨山后消失不见。
“碧血簪。簪上小重楼。
寻得夜幕帐。绣芙蓉。
萧瑟寂寞干醴泉,挂灯笼。”
“你也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人了。”夕说。“古来感叹光阴寸短、白驹过隙的,大有人在。我原以为你们都爱及时行乐,却没想到你和黎,你们都离我而去,这是为何?”
若是自私一点说的话,就是我等不起。我没法陪一个神仙耗费掉所有人生,因为我的全部生命只是那个神仙的一瞬。
但我其实明白我还有另一个理由。
“凡人命短,仙人命长。我不过是自觉我的人生对你不过一呼一吸之间。不再想继续浪费时间而已。”
“你没说实话,黎回答过我这个问题,所以我知道。”
酒杯回来了。带着满满一杯美酒。
夕取杯饮尽。放回流水之中。
“谪仙人,不拜厉王侯。
蓬山雾起落。画中龙。
隆冬夜起语檀郎,枕簟凉。”
“我不信你对我没有留恋。或许你对我的身体还有兴趣。”她说。
不止兴趣而已,与夕的欢合令我流连忘返,我从不羞于承认。我更是多次神游,梦见过那美妙胴体。她在我的身体各处留下过吻痕。若说世间能令我癫狂之物排榜,夕本人绝对高居榜首。
她抓住我的手,抚摸上她的手臂,再到背后,再到肚脐。她既是温香软玉,又是薄冰肌莹,取决于我的手覆盖住了她的哪个位置。
手臂是软玉,肚子是薄冰。我问她是不是肚子有不舒服,她就说:“想来是某人不来应约,许久未饮,胃才犯了寒病。”于是,她掀起肚子上的细软布料,让我直接触摸她的身体。我只得由着她,慢慢抚摩她的小肚腩。
酒杯又回来了。我伸手去接时,她却先抢过去。
“我胃寒,这杯让我暖暖胃。”夕笑道。然后一口饮尽。
“美梦仙,枕思眠——夺两人清闲。”
原来我上次来的时候,她听到了。她却装睡不理我。
“酒醉人,人醉月。”她把酒杯放回流水,“流觥筹一遍。”
已经两杯了,她还没醉倒。
她究竟希望我对她说什么,她还说我撒谎,她早就知道我真正的答案。
我沉默,无话可说。我连下一杯酒时要吟的诗词都想不出来了。心急时,时间也飞快流逝,酒杯马上又回到我们面前。
我伸手去接。
二杯欢伯,最能解忧。下肚后却没让我忧愁消减多少。
“手作画,发结缘。是去年时节。”卡住了。夕朝我嗤笑,还不许我停下抚摩她小肚子的动作。我心烦意乱,时间却并不会等我。
酒杯又临近了。
夕去伸手接盏时,微曲身体,纤纤素手濯过清泉。
“云中云,天外天。解裳睡梦仙。”好歹憋出来一句,算是有点真情实感。
她好像被我的直球逗乐了。
饮尽杯中玉液。夕说,不喝了,喝不了了。
我心想还好。
她说,我想就现在同你困觉。
我将这扣儿松,把缕带儿解,若是入了这温柔乡,自此再也无处逃。我认识夕口中的黎,她说起过那名女性,或许正因如此,她才逃得出夕的手心。不然,等她那白色的长韧尾卷上小腿,谁又敢不合她的心意。
春至人间花秀色。她称我的阳物为俗物,却丝毫不是轻蔑,反倒是露出花开般的笑容与戏谑,玩笑般地说道:“将你那俗物让咱瞧瞧看。”解了裤裆,她就端详起口中的俗物来。在先前抚摩着她的小腹时,我就早早动了情意。
与她的情事并没有我描述那样拘谨,而是十分尽兴,但我若是口出秽语,只怕要招来她不少嫌弃。那我只能借来前人诗句说说:是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折,露滴牡丹开。
又有:但蘸着些儿麻上来,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任恣采。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愠香腮。
唇口软舌香,春床上不做神仙样,便涂了那小姐美甘甘、香喷喷、凉渗渗、娇滴滴一点儿唾津儿满身。
一门心思往下怀想,料到她当做娇娘,情切切,意真真。身盘好似弯月入云中,又是环抱双股间,俗物作芳饵,欲钓瓶中月。欲钓瓶中月,月升半捧雪。月升半捧雪,雪起竹帚动。雪起竹帚动,凌厉穿堂风。是前庭也通,后庭也通。
终于,我坦了白。
“我死了你还会活很久,若你对我不这般情深,你会好受得多。”
夕满意地点点头。其实是她闭眼就能想到的事情,但她非得要听我亲口说出。
“可已经晚了。”
是啊,太晚了,应该在向她索画以前就停了手的。
她明明是个神仙,却将我们相处的每一天都视若珍宝。
“姐姐们说我像极了凡人,才会如此害怕入睡。真要是哪天闭眼后就没了自个儿,没了天地,没了画卷,那我该如何。”
但是。
“但是,如今我睡得安稳,却更像是凡人。”
因为太在意活在世上的每一天。
“可是多亏了你。”
她说的没错,或许是多亏了我。
她向我索爱,也和寻常女人没有两样。
她开怀大笑,不知是在玩笑,还是真心,她在画中慵懒地伸展腰肢,显百般媚态,说:
“相公——今夜纱橱枕簟凉。”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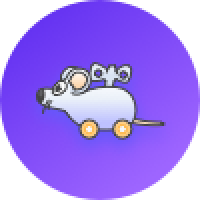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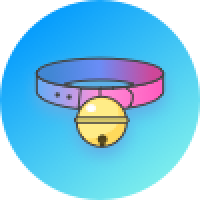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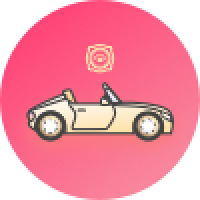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