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记得特蕾西娅手中的剑。
在利剑与鲜血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她得到了些东西,但失去的更多。
不论是给自己讲着故事的特蕾西娅还是那个教自己下棋的博士,都离开了。
还有虽然跟自己渐行渐远,但记忆仍然清晰的爸爸和妈妈。
再后来——
当阿米娅醒过来的时候,自己还是在一个温暖的怀抱里。
背后的黑发女人已经醒了,正在呲牙咧嘴。
眨了两下眼睛,阿米娅才意识到自己身下压着一条胳膊。
“唉?!对不起,博士……”
小兔子下意识的就要起来,结果自己只穿了吊带儿童内衣,又一下子拉起了被子。
“有什么问题,我现在就不是个女人吗。”
博士也坐了起来,她身上只有一件白T恤。
被压麻的右手仍然僵硬的不敢动弹。
“博士,您应该叫醒我的吧。”
阿米娅微微鼓着腮。
“你忙了这么久了,偶尔休息一次也没问题,我哪忍心叫醒你呢。”博士揉着胳膊,“你看,昨天晚上你跟我商量最近的安排,结果就这么睡着了,怎么也叫不醒。”
“……诶嘿。”
阿米娅有点脸红的挠了挠头。
“不好好睡觉会长不高的。”博士笑道,“来,洗漱一下吃早饭吧。”
说着,博士打算先下床穿衣服。
结果她没意识到自己的腿也没什么知觉,差点摔成嘴啃泥。
早饭是非常简单的。
当然这个简单只是相对于食堂而言。
吐司,火腿肠,牛奶,和麦片。
“还要长身体呢,早饭可不能对付。”博士放下盘子。
“博士说话越来越像医疗部的各位啦。”阿米娅嘴角沾了一点面包屑,“不过……真好啊。就像以前一样。”
“等等,你说以前?”博士往吐司上又挤了点蛋黄酱,“……特蕾西娅还在的时候么?”
“对呀。有一次就像这样,殿下,凯尔希医生,博士,还有我……就这么坐在一起吃饭。那个时候,殿下和医生有说有笑,博士反倒比现在沉默寡言太多啦。而且——”
“等等。”博士咽下嘴里的东西,“……特蕾西娅……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诶?”
“想不起来。什么都想不起来。我知道要找特雷西斯讨个说法,也知道我们在传承特蕾西娅的愿望。但是……我想不起来特蕾西娅是什么样的人。这部分缺失了……很奇怪吧。真的很奇怪吧。”
“也确实是这样子……一定会再想起来的吧。”
“没准儿你跟我讲讲我就想起来了呢。”
“嗯……”阿米娅托着腮,“我想想……很温柔的人,有时候像妈妈,也有时候像姐姐。然后呢……”
博士一边听一边喝着牛奶。
他在思考。
吃完早饭之后,阿米娅去处理简妮的入职申请,而博士处理的是另一件事。
在整合运动待了四天之后,霜星终于归舰。
她回来的时候,神情还比较轻松。
“怎么样?”博士霸占了会客室的沙发,一个人坐了两个人的位置。
“——给我腾腾地方。”霜星把博士推到一边,也坐到了沙发上。
“所以怎么样嘛。”
“还好,少部分人还是不情愿合作,虽然就我看来他们只是在较劲。”
霜星最开始还是正坐,说着说着就靠到了沙发背上。
“所以整合运动为什么追着我们到这儿了?恐怕他们不只是想把塔露拉抓去处刑。”博士倒了杯白兰地,轻轻抿了一口。
“伦蒂尼姆的感染者工人不太安分。他们实在是受不了了,又没有足够的实力对抗正规军。”霜星面无表情,“好像各个地方都没什么区别。”
“所以他们寄希望于整合运动的帮助,希望有足够的人数规模对抗贵族的压榨。”博士道,“虽然这么说很没良心……但如果那些贵族想获取长远利益,至少得让这些工人活得下去。”
“听起来很不舒服,但乌萨斯的那群家伙实际上无耻的多。”
霜星并没有看博士。
“所以他们没有远见。”博士的脸也放松着,“虽然我觉得这挺精神胜利的,但再照这么下去他们没什么好结果。”
“然而只靠嘲讽不能令贵族让步。”
“所以这是个绝佳的切入点。你会发现工人们被逼急了力量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他们已经没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霜星向博士的方向稍偏了偏头,“只不过……”
“只不过?”
“只不过他们的愤怒真的能换来什么吗?”
“你不能因为你们被人利用失控了就否定他们抗争的意义。”博士道,“至少知道喊疼,证明他们还是个人。”
“那你倒是说说怎么让他们的抗争不变成感染者的新一代罪名。”
“一会儿让你认识个人。”博士笑道,“有她和塔露拉两个人,我们至少能多三成胜率。”
“最开始是零么?”
“……你还会说笑话呢?”
“不开玩笑了。”霜星歪了歪头,“塔露拉去哪了?”
“艾萨克郡,她还是跟恩特罗菲在一块。据说那边有什么她老爸的线索。”博士道,“我是说亲生的,不是科西切。”
“好吧。”
霜星没再多问。
有些细节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触及的。
“走吧,我说要让你认识个人来着。”
博士站起来,牵住了霜星左手。
一次直击。
一次防御。
一次闪避。
训练场中,两个人打得不相上下,一旁年轻的预备干员正鼓掌叫好。
带有加压管腔的长剑和看上去不好惹的大锤正不断撞出火花。
推进之王的大锤横扫而过,而棘刺避开了这一击。
后退两步,长剑自下而上一记斜劈。
距离已经拉开太远,所以杀伤部位并不是剑刃。
纯白的粘稠液体从剑尖射出。
推进之王一个侧滚,避开液体暗器,一跃而起,大锤直取棘刺头顶。
棘刺已经架起了剑——
“时间到!平局!”
佐菲娅按下秒表之后,刚才激烈对打的两人都后退一步,行了一礼。
“就算打得不错吧。”博士道,“如果不是这种意外情况——”
博士几乎是咬牙切齿。
他面罩上被糊了星星点点的白色,看起来十分狼狈。
“——那不是神经毒素,只是训练专用的记号弹。”棘刺一脸无所谓。
“我巴不得是神经毒素,射了我一脸白问题更大了不是么。”博士一把将面罩扯了下来。
“那只是个意外。”
“把他挂舰桥上去,佐菲娅。”博士皱着眉头,“维娜……干员推进之王,过来一趟,有些事情得谈谈。”
病房中的心电监测曲线十分平稳。
那个伤员的左手搭在被子外面,手腕上感染监测装置淡红的呼吸灯一闪一闪。
被脏弹轰炸后的急性感染过于严重,监测装置已经不是平时的淡蓝色了。
博士维娜霜星三人隔着玻璃看着一片肃杀的ICU内部。
“啊?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吧?”维娜转向博士,“你是准备在我们身上找点什么共性?恐怕不成。”
“也是啊,维多利亚这么大,首都街混子阿斯兰和边缘领地搞恐怖袭击的德拉克没见过也不奇怪。”博士道,“主要是为了另一件事。来,认识一下叶莲娜。”
“大名鼎鼎的霜星,幸会。”维娜伸出右手。
“果然还是我这个名字更出名。”霜星握住了那只手,“维娜,推进之王。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聊天吧。”
“的确。我不曾参加对整合运动的正面作战,所以对你不曾了解。”维娜微笑道,“但博士对你如此信任,我自然也会信任你。”
“还是说点正经的吧。”博士道,“维娜……如果我要格拉斯哥帮回到伦蒂尼姆帮助感染者工人的反抗,你同意么?”
“我们有机会回去么?”
“我说有那就是有办法。”博士看了一眼霜星,“问题在于你们那边。”
“——我知道,整合运动想重建信任在你们看来是匪夷所思的。”霜星叹了口气,“但至少我们得先走出这一步。”
而维娜的脸色并没有什么变化。
“恕我冒犯,但我想这没那么容易。”
“我很理解你是怎么想的。”霜星道,“整合运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所以你不用现在就给出答复。”博士笑道,“只是说我有这个想法。”
“——你确定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么?”维娜掏出棒棒糖叼在嘴里。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确定么?再说了这只是计划阶段。”
“那就把计划再充实一点吧——博士,我想回去睡一觉。”
“睡吧。反正我想告诉你的都说了。”博士又看了一眼病房内部。
“那我就告退——”
“等等。”霜星开了口。
“嗯?怎么了,霜星?”
“你也喜欢吃糖吗?正好我这里还有一些。”
“哦,谢谢。”
鲜红的糖果放在维娜手心,而博士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她已经剥开糖纸将那块东西丢进了嘴里。
之后,眨了两下眼睛,脸色缓和了不少。
“哪里来的糖?挺好吃的。”
“……我的独家配方。”
霜星的嘴角抽动着,似乎是想笑,又似乎是诧异。
塔露拉和恩特罗菲已经完全隐没在了阴影中。
即使是小型移动地块,高度也有将近五十米。
而两个人现在正躲在履带附近。
“两种方案,要么是从底部动力机关混进去,要么就直接上去。”塔露拉仰头检查着四周。
“我选直接上去。”恩特罗菲看着远处的相反方向,“动力机关哪怕没有值班工人监控也少不了,而直接上去只要观察哨转头就行了。”
“可直接上去是这么简单的事吗?”
“跳上去,最多就是五秒。只要找个盲区。”
“你……算了,好吧。”
塔露拉本想说什么,想到前几天从罗德岛离开的时候这个家伙那突破音障的全力一跃又闭了嘴。
得益于附近没有天灾也不是战时状态,哨兵十分懈怠。
但即便如此,城下那一声似爆炸非爆炸的巨响也让他们转过了头。
“等等!你这也太显眼了!”
塔露拉的抗议在气流声中十分微弱。
就像上一次一样,恩特罗菲卡住她的腰就是全力起跳。
高度在不断上升。
眼前的东西从艾萨克郡的履带,防护壁,再到城市边缘,直到他们俯瞰了整座小城。
最高的建筑也不过是教堂,剩下基本都是一二层的小楼。
建筑并不密集,甚至还有花园和人工湖。
恩特罗菲空闲的左手拔出了剑。
在空中随便切了个十字,等塔露拉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出现在了下面的小巷子里。
龙女揉着胸口,她身上疼得就像被大锤砸过一遍。
“下次别再因为我的体质就这么搞了。”
“之前是你说要快点的。”恩特罗菲收了剑。
“我们刚才还在空中——传送?还有这样的源石技艺吗?”
“我想这跟你们那什么源石技艺没什么关系。”
“那你刚才直接用这个不就好了?”塔露拉还是疼的咬牙切齿。
“我是想先确认一下地形,你也不想被传送上来结果卡在墙里吧。”恩特罗菲道。
“你是什么乌萨斯的变态贵族么。”
“什么?”
“把人卡在墙里,然后做些满足兽欲的事儿。”塔露拉冷着脸,“令人作呕。”
“……你怎么知道的?”
“科西切的任务,我把那个人杀了。”
“行。”恩特罗菲往墙上一靠,“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问吧。”
“你之前知道你的教父在这里,还是说你本来不知道,是龙门那边刚告诉你的?”
“后者。”
“——那你最开始是想来这干嘛?”
塔露拉转过了头。
“只是……想看看父亲之前生活过的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你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就是我想知道的。我出生之前他就被人逼死了。但是每个人都说他智勇双全,是个真正能交朋友的人。”塔露拉闭上了眼睛,“而且能让科西切如此忌惮仇恨……想必不会是个庸人。”
“有种说法,人的一生就是追寻父亲足迹的过程,看来又应验了一次。”恩特罗菲道,“既然有目标了,往哪儿走呢?”
“魏彦吾告诉我的是……”
塔露拉抬起头。
她的目光是教堂的尖顶。
“西蒙!弗雷德!卢修斯!人都死哪去了!”
工头的怒骂回荡在核心动力炉的操作间。
原本值班的几个工人都没了踪影,静静工作的设备就像是在嘲讽他。
“这帮小王八蛋,胆子越来越肥了,还敢旷工,真当停了电麻烦的不是他们。”
中年人的厚底工装靴在金属楼梯上的脚步声十分清脆。
等那几个工人回来,被这靴子踢屁股想来不是很好受。
粗壮的双手在衣兜里翻找着,最后拿出来的是烟叶。
工头推开吸烟室的门,想着等抽完烟那几个人还不回来就叫人出去找他们。
结果他硬是没迈出步子。
吸烟室门后突然闪出一个人,手中匕首已经切开了工头的喉咙。
“不错。赶紧换衣服,然后把我们的人接应进来。”
另一个穿着工装的年轻人从暗处走出,他身后是扔在地上的深池黑袍。
阳光透过花窗,在地面上投射着变形的图案。
进门之后,头顶上小平台管风琴的悠扬音乐充盈着整个教堂。
最前排的椅子上,黑袍的菲林神父正低头默念着什么。
而从门外的阳光中慢慢走来的是两个人。
他们的银发反光有点刺眼。
“你确定是这儿?”恩特罗菲右手在眼前挡了一下阳光。
“整个艾萨克郡只有这一座教堂。”塔露拉先一步进了门。
被切割的阳光洒在她身上。
据说,阳光自发出到地面需要几分钟。
所以照射大地的本质是过去的阳光。
而她追寻的过去,也像教堂中的阳光一样,被打的稀碎。
恩特罗菲也进了门。
进门之后,他回头向斜上方看了一眼。
管风琴还是平稳的演奏着。
“——打扰了。请问里希特神父是在这里么?”
塔露拉的语调柔和了许多。
“嗯,没听过的声音,是生面孔啊。”
神父的话语也很柔和,他站起来,转过了身。
他的头发已经带了些灰白。
线条柔和的脸上挂着无框眼镜,微笑着看着塔露拉。
“您……”
“或许我该说,是熟面孔?”
“您也许并没有见过我。”塔露拉也微笑着。
“像,真的很像……只不过,那一位是个男性。”
塔露拉的左手食指轻轻抽搐了一下。
“您……就是里希特神父?”
“或许,你应该喊我教父……塔露拉·雅特利亚斯。爱德华的女儿。”
管风琴的乐声停下了。
恩特罗菲的手已经握住了剑柄。
“那个弹琴的,别走。”
“——我还以为白发的剑鬼是个多么凶猛的人,没想到却是这幅样子。”
随着缥缈的声音,琴手站起来,慢慢转过了身。
恩特罗菲眯起了眼。
“塔露拉……你还记得罗德岛搬走那个受伤的人长相么?”
“很像。倒不如说是一模一样。”塔露拉也转身仰起了头。
如果博士在这里,也许他会惊讶。
惊讶于那个伤员是双胞胎。
“真是不曾想到……雅特利亚斯尚存后裔,失落的德拉克血脉还有更多。”
琴手从二楼翻过栏杆一跃而下。
是个白袍白发的女子。
身后龙尾的末端,一点紫炎正在危险的跳动着。
“你又是什么来头?”塔露拉向前走了两步。
“嗯,我吗?你的确是那个有资格知道的人……”
“少废话,不然别怪我动手,深池的首领。”恩特罗菲冷着脸。
琴手的紫炎燃烧的更旺了。
“情报做的不错。是我的妹妹告诉了罗德岛什么情报,还是小丘郡存有余孽?”
“余孽是形容你这种恐怖分子的。”恩特罗菲冷笑道。
“无妨。”琴手也笑了,“你们可以叫我……维克托娃。”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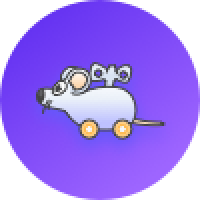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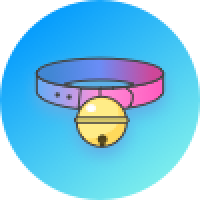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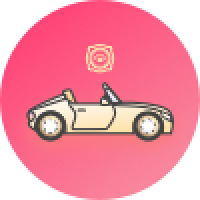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