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笛认为自己的运气一向不太好。
比如在皇家近卫学院的时候,有时候哪怕是单纯吃个饭都能碰到吊灯落进盘子的场面。
对别人来说是喜剧,对她就不是了。
那时候她好像明白了喜剧都有悲剧的内核这个道理。
还有这一次,也许是悲剧,也许是闹剧,但肯定不是喜剧。
从小丘郡逃出去的时候,她只想尽快回到军营,然后把那个真相公布出去。
深池攻陷了小丘郡,并且广播了假消息,将恐怖行为推卸给了维多利亚正规军。
——原本这应该是让长官感到情况紧急的事态。
但结果是等了几天,只等来一堆书面用词。
风笛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于是她离开了。
原定的计划是去龙门找自己的老同学,那个人也许会有办法。
结果是还没路过几个城镇,就跟一群深池部队短兵相接。
而那个打头的家伙两下就打飞了自己的破城矛。
然后就是,自己被他们抓住,一直被押到艾萨克郡。
当再醒过来的时候,自己已经被捆在了木架子上。
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药,总之双手怎么也用不上力气。
这段时间基本是每天被打一顿,虽然每次都斥责这群家伙对无反抗能力的人出手,但好像也没什么用。
如果他们对此有触动,就不会对平民下手了。
风笛有点后悔,离开小丘郡也许该跟上简妮一起走的。
只可惜世界上从没有后悔药。
至于现在深池想干什么,她隐隐有些不安。
“恩特,带着教父先走,我跟这家伙有点东西要谈。”
塔露拉咬着牙。
“你们会打起来的。”恩特罗菲一脸无所谓。
“用不着说出来。”
“那就走吧,神父。”
恩特罗菲打了个手势,里希特神父越过塔露拉和维克托娃走在了前面。
之后的一瞬间,维克托娃的手腕被捏住了。
恩特罗菲似笑非笑。
“你想动手么?你真的想跟我打么?”
“阁下如果不干涉,那将是最好的结局。”维克托娃微笑道。
“那你们俩慢慢聊吧。”
恩特罗菲跟着神父走出了教堂。
而两位德拉克的沉默对峙持续了五分钟。
最后是维克托娃先开了口。
“我不管你背后是谁,但是,能请你就此离开维多利亚么?”
“我的事还没做完,我不能走。”塔露拉沉着脸。
“那不妨把话说开些。”维克托娃微笑道,“你想要什么,不妨也说出来。只要没有冲突,深池会全力帮你达成目标,之后……”
“不管你开出什么条件,我是不会走的。我也没有跟你们这种人苟且的打算。”
“——我们这种人?”
“还要我说出来么?”塔露拉道,“打着大义的名号,普通人看你们却只发现了暴力和恐怖。而如果你登上王座,塔拉人又会怎么样?”
“——你说呢?”
“他们将得到更多的仇恨,而你安然抽身,将对塔拉人的仇恨作为稳定局势的棋子。他们的愤怒,他们的生死,全都被人利用了,直到他们死去也未必会明白。”
“你好像很清楚这些事。”维克托娃还是微笑着。
“因为我曾经就是这种人。我和你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和谈的可能。”
“我曾听闻整合运动的事迹,但眼前的这个人……我很好奇,她真的是那个塔露拉吗?”
“我就是我。我的弯路,我的罪孽,不会推卸给任何人。”
维克托娃的微笑消失了。
“那么,塔露拉·雅特利亚斯……你会不干涉深池的行动么?”
塔露拉拔出了剑。
“——这就是我的回答。”
“——那么,谈判破裂。在维多利亚不需要两个德拉克。”
“还没完呢。”塔露拉深吸了口气,“你想必知道我们两个对你的手下干了什么。被罗德岛带走的那个伤员是你什么人?”
“这,重要么?”
“看来她对你是不重要了。”
“确实造成了一点麻烦,仅此而已。”
花窗就在两人头顶上方。
破碎的阳光让维克托娃的脸阴晴不定。
“德拉克的血脉如此稀少,而那个人长相跟你一样。”塔露拉道,“——那可是你的亲生姐妹。”
“是的。”
“我跟你彻底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塔露拉咬紧了牙,“你在各种意义上让我厌恶透顶。”
“尽管厌恶吧。”维克托娃轻叹了口气,“你的旅程,恐怕也到此为止了——”
话音未落,她飞身一跃回到了二楼管风琴前。
塔露拉跟着一跃而起,长剑从斜下方直刺。
紧接着,她右手被震得发麻。
维克托娃手中多了一杆银色长枪,勉强格开了那一剑。
二楼的木质栏杆已经冒出了火苗。
一身银白的维克托娃似乎微微发着红光。
“——向所有人证明,我才是唯一的纯血红龙!”
离开教堂的时候,恩特罗菲不断的扫视周围。
他的左手没有离开过剑柄。
“别离我太远了,神父。既然深池的首领出现在这,那恐怕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已经全是蟑螂了。”
“看来塔露拉对阁下十分信任。”里希特沉声说道。
“挺复杂的,但没错。”恩特罗菲道,“你对今天的乐师换人好像一无所知。”
“我的确没太注意这方面,因为接到了一些其他消息,想的入神了。”
“我不会说什么你应该看出来的话。”恩特罗菲道,“如果你看了出来并且提醒我们两个,我有理由相信维克托娃会选择直接灭口。”
“塔露拉到底惹上了什么事?是什么人在跟踪你们?”
“——那又是谁将塔露拉的父亲赶出了维多利亚?”
“——”
神父想说什么,但看到恩特罗菲咄咄逼人的态势,似乎又不想说了。
“我不是在问你,只是在整理思路——他们可能是一伙人么?如果是觊觎王位和权力,那么范围能缩得再小一些——”
“阁下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借此找出当年爱德华逃亡的蛛丝马迹?”
神父的表情比刚才微微多了些急切。
“蛛丝马迹还是顺藤摸瓜,这跟我没关系。倒是她——”
恩特罗菲话音未落,先抬起右手拦住了神父。
而神父还是微微带了点困惑。
“出什么事了?”
“——不太对劲。”
“你是指天气吗?一会儿确实是天气预报有雨……”
“天色变暗了,但有什么地方不对。”
头顶的乌云正在汇集。
四周越来越暗,室内的亮度已经不高,但还是没人开灯。
几位住户跑出了家门,交谈的内容似乎是自己家遭遇了停电。
而恩特罗菲慢慢转动着身子。
“你们的移动城镇是有核心引擎的对吧?”
“你的意思是动力炉出了问题——”
神父似乎反应不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号角声突然回荡在艾萨克郡的街头。
声音并不高亢,但听起来让人紧张万分。
火球突然顺着前面的街道直滚过来。
“都从家里出来!往开阔的地方跑!”
火球在行进中爆炸了,冲击波让附近房屋的玻璃裂成了蜘蛛网。
恩特罗菲迎头撞上了火球,接着从爆炸中一跃而出,把术师的脑袋猛拍在了墙上。
“——这是怎么一回事!城镇卫队……他们在干什么呢!”
神父明显是怕了。
但一个和平惯的小镇子突然来了敌袭,不怕的人才是异类。
卫队确实是有所反应的。
街头零星几个人冲了出来,但马上就被暗中出现的深池刺客一人给了几刀。
恩特罗菲已经折回了神父身旁。
“他们看来是断了电,直接让这群蠢驴的指挥失灵了。”
神父的手还有点抖,但脸上已经只剩下了坚定。
“你……能对抗他们么?”
“他们到处都是,你要我往哪个方向去打?”恩特罗菲用舌尖湿润了一下嘴唇,“刚才我看到,城里的中心广场是距离这儿最近的开阔地,对么?”
“确实。”
“那就都往中心广场跑!这附近能藏人的地方太危险了!”
恩特罗菲提高了声调。
“如果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呢!”神父盯着对方。
“他们在那儿聚团,我一个人就能撂翻一支军队。”
恩特罗菲说的轻描淡写,但他还是在警戒着四周。
接着他拖着神父就往中央广场跑。
结果刚跑到地方,他就感觉一阵气血上涌。
中心广场的喷泉旁边竖了根柱子。
一个橙发少女就被铁链子绑在上面。
她的脑袋怎么也抬不起来。
被捆成这样仍然昏迷,而且看不到什么外伤。
恩特罗菲正在怀疑这女孩被打了什么麻醉药。
同时他听到了深池士兵隐约的交谈。
“所以首领还没过来吗!这说好的处刑……”
“再等等……首领不来就我们做。”
恩特罗菲贴近了神父。
“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
“……听不清。”神父的脸藏在人群的阴影中。
“他们要把那个女孩处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既然恐怖分子要杀,我就默认那女孩是个好人了。”恩特罗菲看了一下来路,“看见我们的人应该还没追上来……还有时间。”
罗德岛本舰,医疗部又开始了忙碌。
那个病号突然有了反应,这不得不说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态。
镇静剂和肾上腺素等等都已经准备就位。
博士的脸在面罩之下阴晴不定。
“感染已经遏制住了。”
“可以这么说。”凯尔希站在一边,同样盯着那个呼吸急促的病人。
“但这又是什么反应?”
“我曾经在另外的人身上见过这种情况。”凯尔希看向博士,“你也见过。”
“说清楚点。”
“星极。”
“原来如此。”
博士左拳在右手心狠狠一敲。
即使是在罗德岛,星极的矿石病也是最特殊的那一批。
在她的妹妹感染之后,似乎出于某种源石技艺共鸣,星极同样遭到了感染。
而这个患者——
德拉克的双眼猛的睁开。
她双手痉挛着,几位医疗干员不得不按住她。
口中的音节浑浊不清,但博士隐约还是听懂了。
“姐……姐——”
教堂内已成火海。
维克托娃一枪扫来,枪尖燃烧着令人不安的紫炎。
塔露拉后撤躲过,火舌掠过她的鼻尖,隐隐作痛。
之后她又连退两步,对着头顶挥了一剑。
从屋顶掉下来,燃烧的布幔被她一分为二。
——这当然是破绽,维克托娃抓住机会就是一枪直刺。
即使侧身闪避,塔露拉还是被划开了一道口子。
“雅特利亚斯的后裔,只有这点能耐?”
“——”
塔露拉没说话。
她很清楚这是激将法。
很显然,维克托娃并不是个会在乎损害和平民死活的人。
塔露拉相信,这种人最该去的地方就是审判庭。
——然后呢?
自己原本就是当被审判之身,但恐怕没有哪个国家会公正的审判自己。
她只会再一次成为国家之间杀伐攻讦的筹码。
而维克托娃和深池只可能陷的比整合运动更深。
塔露拉还记得,博士后来将叶莲娜临终前的话告诉了她。
——我们所有人的性命都被利用了。
这让她确定,自己和维克托娃必然是不死不休。
她很清楚,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她不能原谅自己。
长剑横在身侧,接住了对方的长枪下劈。
没有任何犹豫,剑刃沿着枪杆一路上滑,目标是对方手肘关节。
——落空。
两人之间爆出一团巨大火球,将塔露拉硬推出去几米。
花窗本已开裂,在冲击波之下碎成几十片纷纷坠落。
碎玻璃之后,维克托娃的表情带着两分嘲弄。
“——我想不到的是,你连自己的火焰都没胆量燃烧。”
塔露拉还是没说话。
她隐约相信着,停止深池这些恐怖袭击的最好方式就是直接把维克托娃斩杀。
这是个纯粹视人生命于无物的混账。
只要——
——杀意。
她突然想起来,自己在上一次爆发出如此杀意之后发生了什么。
只有那个,绝对不行——
“懦弱,恐惧。你这是骗不了人的。我是该庆幸,还是应该鄙夷?”
“——你什么都不知道。”
塔露拉抬起了头。
火焰已经蔓延上了她脚边的地毯。
她又举起了剑。
“首领……首领在哪儿呢,怎么还没过来……”
“来不及了,你快去找首领,我们这里采用备用计划……”
深池干部的声音隐约传到恩特罗菲耳中。
三个对话的人,其中两个往教堂方向跑,另一个转向了那根柱子。
四周街区朝着这边聚集的居民和深池士兵越来越多。
“——你不是要救她么?”神父贴近了恩特罗菲耳边。
“你知道什么叫最佳节目效果么?”
恩特罗菲调整着呼吸。
他正在为出手积聚力量。
镇民的表情基本都是惊恐和慌张,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莫名其妙被敌人打进来,然后被军刀和弩箭赶到广场,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
而下一步——
恩特罗菲看到那个 橙发少女的头稍微动了动。
她睁开了眼睛,但好像也没反应过来自己的处境。
军号声再一次响彻了艾萨克郡的上空。
有个深池士兵咳嗽了两声。
声音大的不像正常人能发出来的音量,也许是扩音有关的源石技艺。
“艾萨克郡的居民们,我们是深池。”
“小丘郡的惨案各位都已耳闻,维多利亚的军队根本不在乎普通人死活。”
“他们让矿石病的阴霾人为地笼罩了这座城市,他们的所作所为,比天灾更无情更恐怖。”
“我们并不想要战争,但我们不得不反抗。”
“而此次,我们与当时如懦夫一般逃跑的维多利亚军队余孽狭路相逢。”
“虽然不能弥补他们对小丘郡的无辜人民犯下的滔天罪孽,但今日,我们在此将这维多利亚士官处以极刑,告慰小丘郡的亡灵,同时也是宣战布告。”
听到这儿,被赶到这儿的镇民开始了低声交头接耳。
放在正常时刻,没人会相信这群人。
但小丘郡发生的事件是不可能在人心里没有波澜的。
尤其是确定了那不是谣言之后。
这次是小丘郡,也许下一次就是不走运的自己。
只要人和人还有些许联系,大抵也不会说出些小丘郡不服管教罪有应得之类的话。
但这同样也不等于要马上相信这群打进来的深池。
“我们的火焰将净化——”
发着演讲的那位深池士兵被极其粗暴地打断了。
人群中飞出一把锯齿长剑,将他的气管和声带一起切断。
而那个一跃而出的人让几名深池战士在面具后脸色大变。
“这家伙是——”
话音未落,他的脑袋先飞上了天。
“你说我是什么啊?”
鲜血溅在恩特罗菲脸上,虽然是最差劲的化妆,却是分外骇人。
又有几个士兵围了上来,而白发男人余光扫到了一旁的某件武器。
两米多长的破城矛,看起来颇有些分量。
一脚将它踢起来,反手一个横扫逼退几人,接着瞅准了没有平民的方向,将它当成标枪飞掷出去。
一个运气不好的士兵躲闪不及,被矛尖穿胸而过。
血肉和肋骨碎片不规则的四散飞出。
而这一下余力未消,连着后面的士兵一起刺穿,将两人固定在了墙上。
趁着旁边其他人吓住的时候,捆着少女的铁链被一剑斩断。
还不等少女倒下,一条手臂就揽住了她的腰。
“怎么样,还能动么?你是谁?”
“……维多利亚暴风突击队所属,士官……代号,风笛。”
少女的脸色不太好,但恩特罗菲明显感到她并不是全无力量。
“别担心,我知道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就像现在。”
某个士兵刚把弩瞄准镇民,就被砍断的链子砸中后脑,当场倒地。
“……但是,你又是谁?”
风笛声音不高,但听起来还有些底气。
“管闲事的。”恩特罗菲笑道,“怎么样,能动么。”
“不太能用上力气,但是……应该还能走。”风笛撩开阻挡视线的头发。
“在这种地方让我照顾两个不能打架的人可不是什么好主意,这不是等于只能把深池全都干掉了么。”
恩特罗菲扶着风笛站起了身子。
这让旁边的深池战士都退了一步。
“跑吧,还能留下一条命,还是说……想要冲着我走过来?”
人一生中会做很多选择。
但很少有这种机会,选择的两端不是这种死法就是那种死法。
当然人生还有一种万幸。
那就是在这种选择题面前,出现一个突发事件让你不需要再做选择。
灰暗的天空刹那间变为橙红。
伴随着震耳的爆炸声,教堂的方向火光冲天。
似乎是刚才离开的某个深池副官正踉跄着往这边跑。
而染红天空的不只是教堂的火光。
十六七颗火流星正对着广场砸了上来。
“那是——”
“……塔露拉。”
恩特罗菲一咬牙,将风笛轻轻放在一边,接着猛一挥右手。
不可名状的空间褶曲在广场上空慢慢扩大,火流星碰上它,就像是石头掉进池塘。
深池又吹起了军号,但比之前低沉得多。
“首领被打伤了……她说,撤退……”
几名士兵跑去教堂的方向,而更多的人迅速散开,不知去了哪里。
恩特罗菲轻出了口气。
“神父……你可以过来了。”
里希特跑过来的时候,看起来欲言又止。
“这……这是爱德华的源石技艺。”
“照顾好她,我也不知道塔露拉的情况,但我得去看看。”
白发人将风笛扶到神父身边,接着转身就要走。
“那镇上其他人呢?”
“能疏散那就做,救不了也没必要赔上性命。”
恩特罗菲不再回头,径直向教堂冲去。
——这把剑不能再为复仇而生,也没有资格再去主持公道。
——现在手中之剑的意义,在反抗和赎罪。
教堂的门窗已经承受不住里面红龙的死斗,彻底炸开。
燃烧的木头碎片,让塔露拉感觉那就是自己失去的某部分。
两人随着碎片一起落到街上,而站定身子之后,塔露拉把剑又握紧了两分。
艾萨克郡的镇民正在四处奔逃。
烈火之下,无人能逃。
这是生物远离危险的本能。
——切尔诺伯格的居民,那个时候是否也是这样?
塔露拉在困惑。
面前的几乎就是另一个自己,她确实下得去手么?
——杀了她。
不可以。
——这种人最大的贡献就是她的死亡。
那我就不是么?
——继续迟疑的话,会有更多人因为你而横死。
所以我会制服她。
——你还不能真正的面对你自己。
不。
塔露拉的思绪在一瞬间绷断了。
她看到维克托娃又一次发起了攻击。
枪尖扫过不远处抱着孩子逃跑的老太太,几乎在同一时间,两人身上都燃起了紫炎。
——现在她只有一个想法了。
维克托娃也稍微愣了一下神。
在没反应过来的时候,自己的面颊就多了一道血口。
塔露拉已经到了她身后,错身而过时还没忘记往她脸上补一刀。
她相信,如果剑刃再低上两分,被划开的就不是自己的脸。
自从童年那个晚上之后,她再也没有感受到那种毛骨悚然的危险。
慢慢转过身子的同时,她不得不调匀了呼吸。
塔露拉身上的气势已经完全变了。
那双眼睛,就像是见识了这片大地千年般深邃。
“首领!”
“——退后!”
自己真的关心深池的战士么?
维克托娃不知道。
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她还是出言喝止,阻止找自己的人过来送死。
——然而已经晚了。
塔露拉已经做出了行动。
前胸,双臂,小腹,打头的那个副官一瞬间身中七剑。
他已经倒在了地上。
但塔露拉还有第八剑。
从胸口刺下,一直拉到小腹。
趁着那人身体因为剧痛条件反射抬起时,就像处刑一般,一剑断头。
维克托娃又冲了上去。
这一次一定要全力施为——
第一剑砍中的是枪杆,维克托娃倒退几步,双手震得发麻。
紧接着是第二剑,深池的首领已经被打飞了十几米。
塔露拉也冲了过来,剑尖在地面上拉出一串火星。
第三次的格挡,是火焰的碰撞。
赤炎和紫炎的交错让附近十几栋建筑破碎崩解。
——就像是被牛奶泡过的饼干。
维克托娃又退了几步。
这一次的冲击波跟之前完全不是一个等级,让她喉头味道有点奇怪。
猛一咳嗽,结果手背上一片殷红。
这并不是结束。
她已经没有再去算清数字的精力了,只是看到从天而降难以计数的火流星。
感觉自己在向远处的队伍呼喊撤退,却好像又不是。
但她确实也打算离开了。
目标基本达成,把半毁的艾萨克郡留给塔露拉这个失控的疯子也不是一个很坏的选择。
她也许会庆幸这个选择。
因为这样她就不会被卷入更大的危险,虽然她并不知道。
塔露拉在喘息。
附近不论教堂还是民宅,基本上已经不剩下什么了。
这还是她控制输出的结果,如果是像切尔诺伯格一样,恐怕艾萨克郡至少要在一秒之内消失五分之一。
在火焰燃烧的轻微爆裂中,又混杂了些脚步声。
那个声音在她背后几米的位置停住了。
“你还是出来了,塔露拉身上的另一个东西。”
恩特罗菲的声音十分冰冷。
“嗯,是的,我记得你和塔露拉做好的约定。我是否需要使出十二成力气,才有希望从你手下逃得性命?”
声音仍然是塔露拉,但语气明显不是了。
“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打算让她死在这儿。”
背后的恩特罗菲语气仍然没什么变化。
“我想……我也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你会就这样放我走。”
“哼,当然不会。”恩特罗菲冷笑,“我想杀的人,一秒钟他也不会多活。而我想救的人……哪怕他是死了,烂了,我也会从地狱里把他挖出来。而你……”
“嗯,好大的口气。但我知道……也许你真的有那个实力。我……似乎看出你是什么了。”
黑蛇慢慢转过了身子。
烈火中的恩特罗菲只是站着,火光的阴影让他的脸阴晴不定。
黑蛇轻轻吸了口气。
“一切的言语和辞藻,在你面前也许都不起作用……超越了这片大地,真正的神明。”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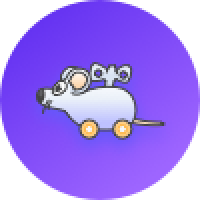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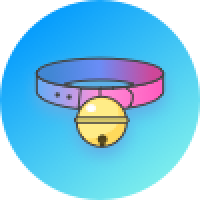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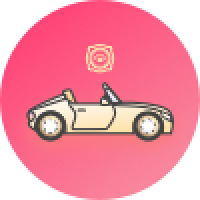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